
与古为徒
Beijing Daily
薛元明 《曾伯簠》在金文中属于“非名品”。所谓“名品”,就是金文系列当中那些耳熟能详,字数又多,风格典型的代表作,诸如《散氏盘》、《毛公鼎》、《大盂鼎》、《季子白盘》等。当然,“名品”并不是绝对固定的,随着新的资料被不断发掘,越来越多的名品会补充进来,这也是书法史的积淀越来越深厚的原因所在。名品通常有“奠基作用”,通俗地讲,就是金文甚至整个篆书系统,必练不可,是绕不开的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,因为取法近似而导致风格趋同。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。为此,着眼点有时须落到“非名品”上——通过名品来奠定笔法、字形的基础,而后各得其所,选择临习大量“非名品”拉开距离。这实质上就是金文系统内“一家为主,多家为辅”的做法,非名品的金文不计其数,选择余地大,加上侧重点不同,每个人选择的先后顺序又有不同,故而风格塑造的余地很大。
邓散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,来不断拓展和完善个人风格。邓散木一生对于篆书的涉猎非常广泛,几乎涉及到篆书所有相关的“子系统”,金文虽然品类繁多,总是有共性所在,这也是得以融汇百家的前提。从临作来看,二者差异较多,原器的圆转浑穆变成了方劲峻拔,且强化了疏密对比,而且从幅式上来看,无疑属于一种“创作式临摹”。从这个疏密关系以及用笔喜用“长线”的习惯来看,主要受到《秦公敦》的影响。也就是说,邓散木尝试用一种金文的笔法来体验另一种金文,这种移形换位、移花接木的实践方式非常独特,可以丰富自身的笔法体验。书法史中存在突发奇想的书家都有过此类尝试:八大山人临怀素,以注释的方式写成楷书;董其昌临颜真卿,把楷书写成行书;徐三庚临《石门颂》,将隶书写成篆书,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。邓散木除了用长笔之外,还喜欢用一招——字形中有多笔同向笔画时,采用“排叠”方式,有利于单个字疏密关系的营造,最终有利于凸显整件作品的“形式感”。
对于有创作经验的名家来说,临摹涉猎越是广泛,创作的应变能力就越强,这正是博涉多家的要旨所在。但不管如何变化,整体上一定要协调。有鉴于此,对临摹范本要做到充分消化吸收,要融会贯通,要能熟练运用到创作中。
小林
从临作可以看出邓散木的化合能力,绝非单纯在金文系统中盘旋,而是着眼和致力于整个篆书系统。金文恣肆跌宕,小篆对称安稳,原本是差异巨大,但在邓散木笔下,各种技法都能和谐统一。
所选两件作品,一为金文对联,一为草篆。金文对联有《石鼓文》笔意,圆劲遒媚,刚柔并济。上下联中的首二字采用了“合文”处理方式,看似“六言”,实是“七言”。“合文”是金文创作中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,《石鼓文》中也有,吴昌硕在临摹时一般保留,创作时比较少见。邓散木可以信手拈来,足见功力精深。此联多用长笔画,字形纵长,气势和疏密不一般,提按丰富。当然,书写的难度也相应提升。这正是所谓的“艺高人胆大”。这件唐王建《江陵使至汝州》诗草篆,为邓散木晚年常见的主要风格之一,将金文、石鼓文、小篆、汉金、隶书甚至行草书和篆刻的处理方法巧妙融合,字形大小、宽窄、正斜等不可预料,随意生发,每行之中,各见变化,但“天头地脚”最终能够整齐划一。这一点,乃是检验书家功力的重要标准之一,行内有“十年平头,二十年平脚”一说,如果是小篆,或者有格子,处理起来可能比较方便,但也容易沉闷单一。这种“天女散花”式的处理,难度大,也因此回味无穷。
邓散木的书论,主要是“实践性”的——关于技法的干货,值得一读。内容涵盖执笔、运笔、读帖、选帖和换帖等方面的经验心得,这是对临摹过程的细化、量化乃至精准化,细致到具体时间的安排。“临摹”对于前人而言,是一种非常“苛刻”的训练方式方法,要求非常高,现在则变得大而化之,名之曰“意临”,而前人最初想到的多半是格临、对临和背临、通临等,从有格到去格,从一个字到几个字的熟练掌握,直至全部熟悉,将字形记下来,然后通临,而后换帖,逐一展开,只有临摹具备了系统性,才有风格的系统性。在临摹过程中,必然会出现和面对一些问题,邓散木针对此类常见的现象,设身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,值得借鉴。从邓散木的角度出发,理论和实践是相互生发和相辅相成的关系,现在的问题是将两方面割裂甚至对立起来,变得毫无关联,各说各话,各行其是,应该引起警惕。温习前贤的经验心得,当是医治这一痼疾的良方。
来源:北京晚报

7月14日,71岁的陈佩斯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,神情中带着无奈与歉意。面对镜头,这位曾用《吃面条》《主角与配角》承包几代人欢笑的喜剧大师,无奈宣布自己阔别大银幕32年后的回归之作——由他亲自导演并主演的电影《戏台》,将从原定的7月17日延期至25日上映,并诚恳地向观众致歉:“对不住大家,让您久等了!” 在视频中,陈佩斯坦言:“时隔32年,我带着新片《戏台》回归大银幕,路演时,看到观众们的笑脸,听到大家的掌声和夸赞,让我既欣慰又感动,每一天都在期待着,电影《戏台》和全国观众见面。但我们得知,这个周末,好几部新电影都要提前上映,《戏台》面临非常大的排片压力,这跟我们当初对这部电影的期待相去甚远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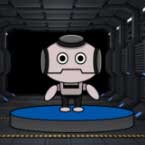 Run 3 Space | Play Space Running Game
Run 3 Space | Play Space Running Game Traffic Jam 3D | Online Racing Game
Traffic Jam 3D | Online Racing Game Duck Hunt | Play Old Classic Game
Duck Hunt | Play Old Classic Game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