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唐诗洛阳记》“复活”古代城市,观看秘籍在这里
Beijing Daily
长安和洛阳作为唐代政坛、文学的双重中心,在中古史研究中之地位自不必说。但近些年来,有关唐朝与唐诗的学术、文学和影视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帝国的上都长安。洛阳,这座低调的陪都(尽管一度升格为国都)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隐于皎日后的月亮。然而若将洛阳拿出唐代,放在五千年的时间坐标系中,便立时能感受到其雄浑厚重的魅力与气魄。她是华夏文明王权与礼制规划下的典范,是“躬修道德,吐惠纳仁”的仁柔之都,历史与文化底蕴都远盛于长安。进入唐代后,洛阳变成了极特殊的存在,从两京并重,到国都,再到陪都,洛阳紧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步伐,气质也从雍容恢弘转为闲适和沉郁。现存的约五万唐诗中,有近五千首与洛阳有关,要理解中国文化之传承,理解唐朝与唐诗,就永远绕不开洛阳。这也是数年前,马鸣谦在构思杜甫、李商隐和白居易三位诗人传记时所注意到的:洛阳是三人行踪轨迹中最重要且余韵深长的交汇点。于是他越过了长安耀眼的光芒,选择洛阳作为其唐代文史、诗人行迹和空间地理书写的主角,为如月光般朦胧的洛阳勾勒出轮廓,重构独属于它的历史瞬间。
在文献史学与考古界,研究一座古都的方式已相当成熟。以长安为例,她的身形样貌可借助考古勘探重塑,其精神灵魂可从浩如烟海的传世典籍、敦煌发现的文书与壁画推想。洛阳之研究也差不多如此。那么,作为普通读者要如何去观看一座古都呢?
谭其骧先生在1986年发表了《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》一文,指出:中国文化不等同于“封建时代之文化”,亦不是只有“儒家文化”和“汉族文化”,地区与城市的风土习尚因生活其中的千万个体而千差万别。如何从规整的城市布局、客观的史料记述中找到一座古代城市的独特气质,是认识和观看它们的关键。
比起礼法制度理念下整齐统一的城市规划、形态与空间结构,城中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是更为有趣的观看角度,如加缪在《鼠疫》中所说,认识一座城市即是看人们怎样生活、相恋和死亡。而当中古城市居民的自我记述缺席,文人官员围绕城市写下的诗文就是认识它们的最好媒介。以唐诗为线索,将唐诗“放还”发生的地理空间,就是《唐诗洛阳记》为我们找到的方法。
《唐诗洛阳记》中,洛阳并不完全是诗的叙事对象,大多数时候诗人们只是抒发自身情感与描绘生活,并非在有意识地以“都会诗人”身份创作专属于洛阳的文学。阅读和赏析唐诗时,读者会从表面看到李白在秋夜宿于龙门香山寺中,是夜水寒波急,木落山空,他的诗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凄凉萧索;韩愈在某天出城钓鱼,从“平明鞭马出都门”到“晡时坚坐到黄昏”,原本安逸的时光竟让他生出遑遑半世的隐哀;当诗背后的动因与场域消失,对“诗”本身的理解只能流于空洞和机械,同样的城门、月光、山景和水流可以出现在任一地点和朝代。如果将这些诗歌“放生”回诞生的现场,一切就会豁然开朗:李白此行是在多年后重返曾遭遇“北门之厄”的洛阳,是长安求仕失败后辗转于此;韩愈时年居住于妻子娘家,位于洛阳城南的敦化坊,北上垂钓于“有王之盛德而先温”的洛水,触景生情,才倍感举选之徒劳。洛阳不是诗人描写的对象,却是诗人故事无法回避的内在逻辑。因此,如繁星散落于浩渺典籍的洛阳诗歌在《唐诗洛阳记》中被编排重组,无数唐人生活的碎片像斑驳的光影交叠投射于洛阳这张幕布,最终形成完整的历史与地理叙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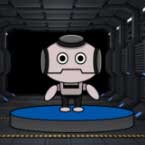 Run 3 Space | Play Space Running Game
Run 3 Space | Play Space Running Game Traffic Jam 3D | Online Racing Game
Traffic Jam 3D | Online Racing Game Duck Hunt | Play Old Classic Game
Duck Hunt | Play Old Classic Game






